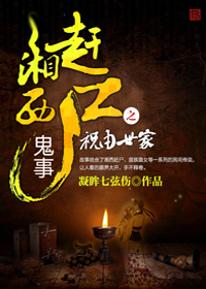靖明 第214章 重新打天下
- 背景色
- 字号
小 默认 中 大 特大
- 宽度
640宽度 800宽度 默认宽度 1028宽度 1440宽度
- 滚动
双击开始/暂停滚屏
第214章 重新打天下
第214章重新打天下</br>崔元在养心殿内坐立难安。</br>京营的事,杨廷和他们再怎么担心,在如今这种情势下也不敢插手——虽然是戏,但陛下岂会真任由新党掌控越来越多的实力?</br>一切都只能按照皇帝计划好的方向和步骤去行动。</br>“陛下,三道旨意过去,莫非早就……”</br>自从成为勋戚在国策会议上的代言人,崔元日益成为大明不可或缺的一人。</br>勋戚这个大群体,都指望着崔元为他们争取利益。</br>可现在形势越来越明显了,陛下从一开始都不只是想推行一下新法富国强兵。这局棋,藩王宗室、勋戚、儒门官绅,无不牵涉其中。</br>崔元想不通:陛下为什么要这么猛烈地刨自己的根基?就因为眼下参策们威望都够,所以要毕其功于一役?</br>惠安伯张伟及五军营里那些想赚军功但其实无能的勋臣若以谋逆之名被办了,在天下勋戚心目中无异一场大地震。</br>仅仅新党可办不到这一点,陛下是必须出来表态的。</br>阻拦新法就相当于谋逆,这不是一句曾有明旨就行的,这必须是皇帝真实的态度。</br>不用继续留有余地了吗?</br>朱厚熜搁下了笔,抬头说道:“周师病重,这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br>崔元愣了一下:周诏周希正?为什么突然提起他?</br>“正德十六年,周师劝朕以国本为重,要善待勋戚,富国之志不可操切。”朱厚熜轻叹一声,“本来年纪虽大,但身子骨硬朗,是有希望度过耄耋之年的。只是朕决意如此,周师还是忧虑过甚。”</br>崔元满脸苦笑:“陛下,纵然参策们大多都已老迈,总不至于青黄不接。李翔之事虽突然,然处置如此刚猛,恐中了贼子奸计。”</br>人家要的恐怕还真就是天下压力就此被点燃、宣泄出来,让朝廷面对一个四处起火的大明。</br>朱厚熜却说道:“朕要的新法不是请客吃饭,商量退让。懋仁,你没有德华看得准。”</br>崔元回想着王琼发表过的言论。</br>就是天下岂能不流血的那句话吗?</br>但何必从最依赖于天子信重的勋戚开始着手?</br>“陛下之意,天下若无反贼,杂草除之难尽?”崔元问了一句。</br>所以一开始费宏说着天子要留有余地,但陛下想的却是诱一些人反吗?</br>朱厚熜只是冷漠地说道:“侵田夺店,犯禁走私,祸害百姓,到地方上要辛苦找多久的实据?办事的上下官吏,又有多少会尽心用事?张孚敬在广东杀了两趟,又有大增官吏、鼓励行商分化之,今年广东赋役共担尚需都司、治安司以武力相压制。这是触动根本利益的事,朕从没想过可以堂堂正正、平平稳稳便能推行下去。”</br>他看着崔元,仿佛看透了一般说道:“哪怕中枢君臣一心,推行到地方也无济于事。能到县的皇权,本身也只是无损于他们利益的一些政令。这些事,朕清醒得很。新法能不能成,不在于先后施行的顺序,不在于参策能否一心用事,不在于有没有一场戏演给天下看。涉及根本利益,戏会被当做真,朕根本没有余地。守旧制的皇帝,对天下已经占据着利益的人来说才是好皇帝。”</br>崔元沉默难言。</br>皇帝能对他说这些话,是把他当做真正的心腹。</br>可他实在担心办了张伟等人之后的连锁反应。</br>京营,做好平叛准备了吗?</br>粮饷,又怎么办?</br>真正推行新法,有许多条路可以走,但陛下要选择这么暴烈而仓促的一条。</br>他还说没那么险。</br>“新法能不能成,最重要的是决心。”朱厚熜顿了顿之后说道,“历朝历代,皇帝重用臣下推行新法,都是留有余地。涉及到皇权根本,旧党有所倚仗,新党终究难以竟全功。杨阁老没有哪一天不盼着朕站出来告诉天下人,就是朕一心要行新法,他只是个忠君的贤臣。”</br>这一点崔元也承认,杨廷和每天都在肉眼可见地变老。</br>“京营既已初成,朕就不必再如之前一般了。”朱厚熜看着他,“懋仁,朕告诉你几句话,你用心体悟。”</br>“……臣谨听圣谕。”</br>“其一,立国已过百又五十余年,朕推行新法,无异于重新打天下,而非守江山。”</br>崔元默默听着:以正统皇权,以新练京营再次打天下?</br>朱厚熜继续说道:“其二,立威比养望更容易,天下可先畏朕之威,再怀朕之德。”</br>崔元想着王琼、杨廷和等人转变的过程,发现也是如此。</br>“其三,朕杀出一片新天,天下百姓及真正期盼新法和新机会的文臣武将才能跻身显贵,一心忠于朕。”</br>崔元抬头看了看那始终悬挂于御书房的天下舆图,缓缓开口:“大明未能开疆拓土再创新利之前,新法若要成,便只能夺之于旧有权贵官绅。以陛下实践学来看,私欲也是恒在恒变,故而没有谁会真的束手待毙。此前之平静,无非在等一个时机,等几个带头的人,先试试能不能从党争中获胜。”</br>朱厚熜点了点头:“其四,始终要清楚,对新法不满者,并非百姓。而百姓觉得新法好,大明江山就不会乱。穿鞋的,伱们忧从何来?大明不缺柱石,只怕没了根基。”</br>崔元缓缓站起来,行礼说道:“臣明白了。陛下之意既已决,臣便去同杨阁老、大司徒等商议粮饷之事了。”</br>朱厚熜笑了笑:“正该如此,不必在这等着张永的消息,定国公不是也去了吗?朕三年前所说密库,岂会真死板效仿赵宋、为北虏而设?天下安定,新法有成,大明何愁不富?钱,用出去才是钱,卿等放心筹划便是。”</br>“……臣斗胆问一句,内库已然借支户部不少银子了,陛下还备了多少?”</br>朱厚熜已经继续低头写字:“京营纵然尽数双饷也无忧。况且,如今是专打大明上下最富的一群人,粮食,银子,他们家里都不缺。”</br>崔元只感觉头皮发麻。</br>话糙理不糙,这确实不是打贫苦老百姓。</br>现在他也有点悟到了,为什么陛下不像杨廷和认为的那样,始终准备演着、尽量平稳地把新法推行开,而是非要诱出一场大乱来。</br>因为有心算无心之下,平叛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慢慢去审案,只需要兵。</br>谁刚刚冒出来,就直接砍过去。</br>这才是真正的快刀。</br>陛下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以早就承平百年的大明来说,这么多养尊处优的富裕人家,想反的尽管跳出来,他只怕担心跳出来的不够多。</br>要不然,新的文臣武将如何往上爬?</br>得利于陛下,才会真正地忠于陛下。</br>崔元离开不久,养心殿后院那边就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陛下,臣妾好过来吗?”</br>“……怎么了?朕这里没人。”</br>文素云碎步跑过来,带出一串清脆的头饰和玉环响声,身后还跟着孙茗身边的章巧梅:“茗姐姐要生了。”</br>朱厚熜顿时搁下了笔:“太医院那边、稳婆那边已经吩咐了吗?”</br>“已经派人去了。”章巧梅赶紧回答,“陛下,皇后娘娘有些怕……”</br>朱厚熜哑然失笑:“看来是朕念叨年纪小孕产凶险太多了。也罢,朕先过去看看她。”</br>说罢就起身对黄锦说道:“先帮朕收好。”</br>文素云奇怪地瞄了一眼御案上的纸张,只见上面都是一格一格的字:“陛下,臣妾听说今天议着很重要的国事,你还在习字啊?”</br>“……操心得多了吧你?”朱厚熜揪了揪她的脸,“先回你宫里呆着。”</br>这丫头就是见着什么都喜欢多一句嘴。</br>奉天殿外的武楼那边,崔元把杨廷和、蒋冕、杨潭、吴廷举、王宪、李鐩等人都请来了。</br>在武楼而非文楼,说明这是军机大事。</br>听崔元说完情况,杨廷和忧喜交加:“陛下真如此说?”</br>“张公公以那等言语前去问话,张伟要么束手待查,要么必然铤而走险。”崔元凝重地点头,“如今无论如何,陛下要借张伟唆使李翔阻挠新法一事办几个勋臣已成定局!各省总兵官及边镇勋臣任职者众,消息传过去虽然还需要些时日,但有心人只怕会加紧鼓噪。京营要即日起开始筹备平叛事宜了。”</br>杨廷和惊喜的是陛下准备站到前面来,不让他这个党魁承担那种权倾朝野的名声了。</br>但他担忧的和崔元一样:皇帝引诱自己的臣下谋反这是什么操作?</br>道理虽然都懂,但柱石毕竟是此刻拱卫着皇权的柱石啊!</br>杨廷和等人毕竟年老,他们一辈子都在“事缓则圆”的妥协原则中走过来。</br>